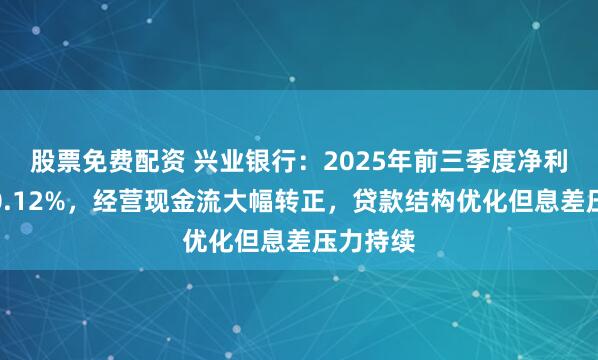公元957年,正值后周世宗显德年间,风云激荡甫定,大名府莘县(今属山东)的一方庭院内,兵部侍郎王祜(王祐)亲手植下三株槐树。新苗挺立,王祜目光深邃,抚树朗声道:“吾后世子孙,必有位至三公者!”。不仅有对后辈的期许,更是一种植根于儒家理想的精神锚定。
是年,其次子降生,因生于凌晨,故取“旦”字为名,字子明。幼时的王旦,虽沉默寡言,却好学不倦,且聪慧异常,深得王祜喜爱,“此儿当至公相”。
时光荏苒,四十载春秋流转。王旦果然不负父望,于宋真宗景德年间(1004年起)官拜宰相,执掌帝国中枢长达十二载,成为北宋“咸平之治”后期至“澶渊之盟”后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柱石。其风范连真宗皇帝也深为倚重,曾目送他退朝的身影而由衷慨叹:“为朕致太平者,必斯人也!”
展开剩余88%庭院中,当年王祜手植的三槐枝繁叶茂,亭亭如盖。那婆娑的绿荫,所庇护的又何止王氏一族的门庭荣耀,更深深荫蔽并象征着一个时代士大夫所追求的理想气度。
01、正直:权柄之上,正直为碑太平兴国五年,王旦进士及第,后出任平江知县。甫一上任,王旦便不负其美名,颇多善政。当时“属吏屏畏”的赵昌言对其称赞不已,不但将女儿许配给他,还多次在朝堂上举荐他。
王旦凭借过人的才学和品德,仕途顺遂,每任一地,皆有善名。咸平三年,王旦奉命主持贡举后,被授任给事中、同知枢密院事,正式跻身北宋政治核心。此后,连任要职十八年,及至病逝。身后又获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、魏国公,谥号“文正”。 乾兴元年,配享真宗庙庭,宋仁宗题其碑首为“全德元老”。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。
“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辅相两朝,天下所知。”
执掌中枢权柄十八年,王旦的府邸却萧然如寒士。史载其宅“仅能避风雨,全无雕饰”,所用床席被褥皆粗布旧毡,家人欲以绸缎包裹坐席,他正色拒之:“吾位虽高,岂可忘布衣本心?”其弟王旭见朝臣皆佩玉带,便私下购得华带一条送给他。王旦不斥不怒,反而笑着令弟弟自系华带于腰间,反问道:“可睹其华乎?”答曰:“系于身,安能自见?”王旦于是轻叹:“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,无乃劳乎!”其弟幡然醒悟,当即退还玉带。
甚至连宋真宗见其屋舍破败,屡次欲以国库金修缮,也遭到拒绝。“寒舍虽陋,乃祖辈遗风,臣不敢以相位易家风”。
王旦深知“金玉之累,不在耗财,而在囚心”的道理,因此不但在生活中保持清贫,朝堂之上亦保持绝对的清醒自律。
其侄王睦求举进士,他严拒:“吾门已显,岂可夺寒士之阶?”;女婿苏耆落榜,枢密使劝其向真宗进言,王旦正色道:“国家以才取士,自有法度。我为宰相,若徇私举亲,何以立朝纲、服天下?”立殿默然。后苏耆凭文章自试及第,满朝方悟其苦心。
天禧元年(1017年)临终之际,真宗赐金五千两。王旦上表辞曰:“生民膏血,安用许多?益惧多藏,况无所用!”,强命家人奉还内库。及至赏银复抬至府门,人已溘然长逝。棺椁之中,唯布衣素衾,无金无玉。原来,他早已嘱托子孙:“盛名清德,当务俭素,保守门风”,为此,还拜托密友杨亿监督丧葬,免俗礼奢费。
其子王素泣叹:“先父之清,不在辞金,而在畏金”。畏者,非惧财蚀德,乃惧德不配位。玉带可还,田宅可弃,“全德元老”四字亦可凿穿千年时空——真正的权柄从不在府库之丰,而在人心立碑之时;清名之重,重于千金,更重于万代家声。
当然,能以“太平良相”之名载入史册,不只是因为其正直清廉,更在于他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的雅量,不仅能化解朝堂纷争,更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出一曲君子坦荡的绝响。
02、豁达:沧海纳川,星月同辉寇准与王旦同年进士出身,却因性格迥异屡生龃龉。
寇刚性烈,常于真宗面前直指王旦之失。某日,中书省递交枢密院的公文因格式有误,寇准当即上奏,引得真宗斥责王旦。王旦未作辩解,反而“引咎自责,堂吏皆被罚”。没过几日,枢密院送中书的公文亦现疏漏,属吏欲借此报复,王旦却淡然命人退还修正,“瑕疵当正,何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?”寇准闻之面赤叹服:“同年,甚得许大度量?”
然而,此非止容人之量,更见王旦“重公义而轻私怨”的格局。他深知寇准直谏实为忠君,因此,当他一病不起,面对病榻前真宗“卿今疾亟,万一有不讳,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?”的问询。仍勉强起身对曰:“以臣之愚,莫如寇准”。真宗认为寇准刚直狭隘,且曾经与王旦多生龃龉,希望王旦再考虑其他人。王旦却坚称,“他人,臣所不知也”。
后寇准为相,真宗明言乃王旦所荐,寇准“惭谢不已”,终悟同年的星辰襟怀。
王旦的豁达也绝非乡愿庸常,《宋史》评其“人有谤之者,辄引咎不辩;至人有过失,虽人主盛怒,可辩者辩之,必得而后已”。他不辩谤言,因畏私心蔽公义;力辩冤屈,因惧忠良蒙尘垢。以不辩之姿涤荡朝堂之争的阴霾,以公心之诚浇灌贤良之士的沃土,终令北宋政坛清流奔涌,开“咸平之治”的盛世气象——德才兼备的至高之境,从不在庙堂之巍,而在心域之广。
而支撑这份恢弘气度的,则是王旦在治国理政中的超凡智慧。
03、智慧:弦弓无声,破浪无痕真宗中后期,宋辽进入和平期,真宗决心封禅泰山。契丹听闻,奏请每年另外给予钱币,以试探宋廷虚实。朝堂之上,群臣激愤如沸,斥其“贪得无厌,当断然回绝”。独王旦目光如炬,洞察其背后玄机:“东封甚近,车驾将出,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,止当以微物而轻之。”然后,允借银绢各三万,明言“次年额内除之”。辽使窃喜北归,自以为得计。然次年岁币交割之期,王旦令边吏悉数奉上全额,并遣使递书:“契丹所借金币六万,事属微末,今仍依常数与之,后不为比。”契丹深感惭愧。
轻描淡写间,将危机化为无形,辽国君臣不仅无由挑衅,反露畏缩之态,终不敢再生事端。此举如“弦弓无声”,以寸缕之利固千里河山,史载“使契丹无词可藉,亦无衅可开”。
王旦“不掀惊涛”的智慧,更在国策制定间从容施展。
天禧年间,“茶法改制”之争如疾风骤雨,激进者欲废榷行商,保守者则主张固守旧章。王旦明面秉政持平,驳回了操切之议,似守旧制;然胸中丘壑早已落笔成策。数日后,一道事关他务的奏折呈于真宗御案,君王展卷间,忽见夹页处附有《渐进改良五策》,条分缕析:分年减税纾民困、设仓平抑抑豪强、严惩兼并固边贸、以茶易马安边防、整饬吏治防贪渎。真宗拍案称绝:“火急则焦,缓火方得真味!”
这“夹页密策”,犹如一股韧劲十足的暗涌,在十年变革中推陈出新,茶税倍增而民未困,于无声处滋养着大宋的经济根基。
大智似愚者,不掀惊涛而移山海;弦弓无声处,自有风云满雕鞍。
王旦始终以“遵法守度,重改作”为圭臬。其智慧如江河暗流,不震山岳而塑其形,不裂金石而涤其垢——北宋百年基业坚若磐石,其中自有这“弦弓无声,破浪无痕”的磅礴力量。
这份举重若轻的治国智慧,其根源之一,在于王旦识人用人的精微。
04、精微:暗室悬镜,毫末识材王旦位极人臣,其交往必定高朋满座。然与众不同的是,谈笑风生之间,王旦那如炬目光始终澄澈清明,默察才俊之士的言谈举止、胸襟抱负,不动声色地将那些蕴藏经纬之才记于心间。
当才华横溢的状元张师德,因两度求见被拒而情急之下托请重臣时,王旦闻之并未动怒,唯余一声叹息:“惜乎!堂堂状元气度,竟也沉不住气,汲汲于此等奔走钻营之事”。面对众人不解其暂缓张师德升迁的举措,他正色道:“状元之才,朝廷岂会埋没?然若此风一开,人人皆效,那些出身寒微、无门无路却真正有才学的贤士,又将何望?”(《宋史·王旦传》)王旦所虑,乃是维护选贤任能的清正本源。两年后,待张师德心性磨砺渐趋沉稳,王旦方审慎擢升其位。日后,张师德政绩卓著,方悟当年王宰相的良苦用心,看似“打压”,实是对其心性定力的淬炼,更是对朝廷风气的守护。这份对心性细微之处的洞察与淬炼,正是王旦精微之始。
洞悉人才特质,不以常理度之,而以器局匹配,非止于明察秋毫的慧眼,更在于为国举才的深远考量与不矜不伐的深沉担当。
在王旦举荐的人中,先后有八人拜相(如王曾、李迪等),其余如李及、凌策等亦成一代名臣,功业彪炳。尤为动人心魄者,被王旦慧眼识中、暗中推举而身居高位者,大多竟不知自己的伯乐是谁。
王旦深谙“荐贤如种树,不夸沃土,但待成荫”之道。不争伯乐之名,不居举荐之功,唯以社稷苍生为念,将真正的国之栋梁默默托举到历史舞台中央。
识人于未显时,方为真伯乐;荐才而不居功,乃是大境界。 王旦的识人之术,不仅烛照人心幽微,更辉映出为政者最珍贵的品格。
当金兵踏破汴梁时,王旦六世孙王伦昂首走向金营:“吾祖清风在骨,岂惧刀斧?”十次使金不屈而死。
三槐堂今犹在开封曹门外,槐叶岁岁枯荣,其根脉早已深扎大地——
正直是权力的压舱石,在物欲横流中锚定初心;
豁达是格局的试金石,于党争倾轧间开辟清明;
智慧是治世的指南针,于变局混沌里点亮星图;
精微是用人的听诊器,在众声喧哗中听见真才。
王旦以“太平良相”之姿,用一生时间将三槐的期许化为“全德元老”的现实,熔铸成一座穿越时空的士大夫精神丰碑,其深植于华夏文明沃土的精神根脉,将永荫后世,启迪千秋。
发布于:河南省驰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